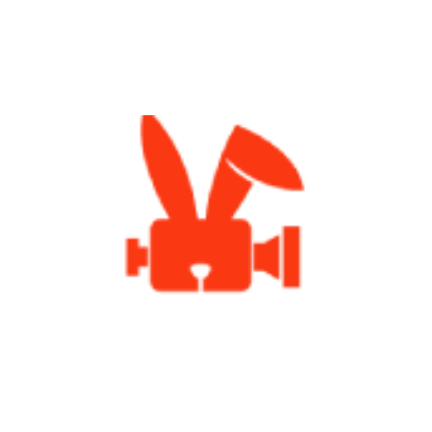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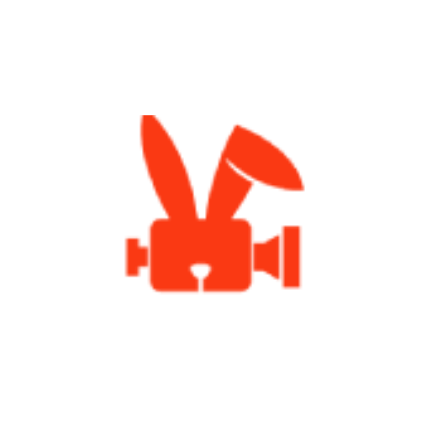
《荒野猎人》后的第十年,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在近期上映的《一战再战》中,再次现身国内院线。这也是「鬼才导演」保罗·托马斯·安德森(PTA)的作品首次被国内院线引进。
对于一位商业属性并不突出的导演,耗资1.3亿美元的《一战再战》成为PTA迄今为止投资最高的电影,也是PTA首部尝试走向主流商业电影的作品。
故事始于一场激进的革命战争。十六年后,这场革命「后遗症」复发——围绕生父不明的少女,展开了一场几乎席卷当年所有人的绑架案。
「革命领袖」与「镇压首领」两个「父亲」的精神图腾,时隔多年后再次正面交锋。当少年衰老,当激进的革命热情,随着年轻气盛,离他们远去,「聊发少年狂」似乎成了某种力不从心的奢侈。
这部颇有些荒诞喜剧味道的电影,沿袭了PTA的一贯风格:将宏大的历史叙事,浓缩进抽象的个人经历与内心世界中。美国权威媒体认为,《一战再战》将是明年奥斯卡非常有力的竞争者。
这样的风格,也让还愿意走进影院的影迷观众们,感到一丝安慰:电影依然如此有张力,可以包裹虚幻与真实、悲壮与戏谑、历史与现在,既有承载复杂严肃叙事的能力,同时将故事讲得轻盈、没什么爹味、并不无聊。

严格来讲,PT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导演,而更偏向艺术大师的传承路线。
1970年,他出生在加州影视城,色情工业最发达地区。父亲是当地电视节目的主持人、广播播音员与演员。在耳濡目染下,他八岁开始拍影片,曾在纽约大学电影系就读,但没过多久便潇洒退学,用退还的学费拍摄了《咖啡与香烟》,获得了好莱坞关注。
2012年,PTA凭借《大师》拿下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银狮奖,成为影史上首位拿下柏林、戛纳、威尼斯三大影展最佳导演项目的作者。被称为「鬼才导演」。
在那之后,PTA 再以《大师》《性本恶》等别于以往类型的影片掳获影迷。从影射宗教故事、到反映嬉皮文化,囊括整个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文化氛围,其内容、风格与形式在「左与右」光谱两端不断流窜。
PTA像个挖掘历史幽灵的考古学家,将美国现代文化史,凝结成正在发生的寓言。他以群像结构、风格化影像,层层挖掘美国文化内的创伤、信仰与欲望──还有反复被压抑、却始终蠢蠢欲动的暴力。
在PTA的创作谱系里,《一战再战》既延续长久以来对美国社会与人性的凝视,又在风格上开出一条新路。
举重若轻的叙事风格、抽象、浓缩、符号化元素的呈现,让他看起来是个善于解构的创作者。但其处理议题时的态度,却是严肃的、古典主义的。这中间的张力,让PTA的影片显得愈发迷人。
若将《一战再战》与《血色将至》《性本恶》来看,几乎是构成美国百年历史的隐形三部曲──从资本狂潮开端,反文化幻灭,到意识形态撕裂的当下,映照出不同时代的权力暗流与精神创伤。
隐喻
《一战再战》登陆国内院线,让PTA的作品从「一向远离主流」,到有了直面更广大的中国观众的机会。其中相当一部分,并非其影迷。
有观众看完电影后,在社交媒体称其为美国版《让子弹飞》,呈现了革命十六年后、不甚体面的续集。在对历史事实的抽象浓缩和隐喻式展现上,二者确实有相似之处。
某种意义上,PTA确实称得上给美国六十年代后文化史著书立传的导演。
《一战再战》的隐喻符号十分丰富。
故事时间背景被放在当下,所发生的事件,却是1960年前后的种族革命,机器引发奠定侯文华运动。
「法兰西75」这个组织名,既暗示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,又暗示其与法国大革命属于同一革命浪潮的渊源。而这,也奠定了美国 「革命派」与「保守派」自建国起就存在的路线斗争。
PTA的特色之一,在于喜欢将宏大的历史叙事,凝结于某些极具代表性的个人生活、内心冲突中。
革命中的三方势力,被PTA浓缩为三个具有明显指向意味的角色,平等地表达着嘲讽与不满。
黑人革命领袖帕菲迪娅,与革命派帕特志同道合,却与白人军官洛克乔生下女儿。
她无时无刻不在释放性吸引力,在炸毁电塔时向帕特求欢、因洛克乔对自己的痴迷而满足,却在抢劫银行时轻易枪杀同为黑人的保安,导致自己被捕。
以帕菲迪娅为指向和代表的左翼力量,激进、真诚地错将欲望当作理想。她将政治谱系与性和刺激挂钩,革命理想中夹杂着大量的炫耀和自恋,并非自我标榜的那般高尚。

而以洛克乔为代表的圣诞冒险者俱乐部,则是美国极右翼力量的缩影。
虚弱、软弱,野心勃勃却像个巨婴,小心翼翼维持着脆弱的优越感。老白男组织直言,加入他们,便能获取「人上人」的特权。但背景尽调也异常严格,除了光环与标签,最重要的是血统纯正、不容玷污。
帕特所的左派革命者,虽推崇「自由信仰」,却也「自甘堕落」,暗喻着昔日革命者内部的迷惘。
他们颓废、迷茫、好高骛远,对《阿尔及尔之战》的台词印象深刻,却对身边的女儿一无所知。当精神上无法与当下和解,便选择用烟酒麻醉自己。
这组畸形的三角恋,也暗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中,黑人阵营因过于激进而被美国政府清剿,与美国政府结合,诞生以「白左」为主体的「混血儿」——新自由主义。
他们尽管活在一个平权为主流意识的时代,由「进步」的父母养育成人,却并非革命者血统,而是叛徒与白人的产物。
相比之下,以Sensei为代表的拉美移民力量,似乎更接近真正的革命者:与「法式75」的混乱、古板、业余截然不同,Sensei永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、为谁而战,永远气定神闲。
以不同身份标签,作为不同群体在社会中位置、阵营的政治浓缩与抽象隐喻,在PTA其他作品中,也表现得十分明显。
如《血色将至》中,男主丹尼尔代表资产阶级原始粗暴的积累,自大、贪婪、不择手段;而传教士则代表借宗教蛊惑人心的小人。通过对「上帝已死」过程的呈现,让观众直观感受到资本、工业对于信仰的颠覆。
对于PTA而言,美国精神的内核中,存在着一场永无止境的拉锯战。革命、反抗是一种循环往复、代代相传的遗产。
今天发生的一切,都不是全新的,而只是历史循环中的又一个节点,是对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新一轮反刍。
PTA的影片,虽然带有嬉皮文化风格的轻盈,但并非将视角聚焦于个体化叙事,而是基于宏观、抽象的政治视角,对美国当代历史进行梳理、总结、反思。
他对过往的态度,始终带有戏谑,却并非虚无主义,而是追求与历史达成某种宗教性的和解——或许是另一种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」的英雄感。
为了找到锚点、让电影看起来更真实,PTA 不断在以明确、风格化的手法,将过去某段特定时期的意识历史化,将后现代主义美学作为时代的影射。让影片中的场景看起来明明是美国,却又似乎是某个架空的反乌托邦。
《不羁夜》中频繁出现的色情演员、妓女或性爱电话女郎,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比尔.克林顿引发的色情时尚风潮。一路到《血色将至》中二十世纪初的石油热、《大师》中二战后的美国、《性本恶》中的嬉皮文化、《甘草披萨》中的石油危机与水门丑闻……
PTA用作品串起了大半部美国历史,却并非在向历史致敬,而是将其再现、希望通过对彼时彼刻的重新诠释,展现对过去的缅怀。在这些作品中,他对过往的浪漫化呈现,远比对那段历史本身更感兴趣。

他以轻盈的口吻,将革命、政治,消解为情欲故事。所谓自由、理想、改变世界,在PTA眼中,无非是无处安放的性压抑。并没有那么神秘、高尚,更谈不上伟大。
而这,似乎是他一直想挖掘的,深藏于美国建国神话之下的创伤根源。一如《血色将至》中资本主义的原始暴力《大师》中战后的精神空虚。
整个国家的历史与风格,就是他的公民身上那些微观心理创伤所聚集而成。
要理解美国,就必须理解驱动美国历史进程的个体。这些人往往内心残缺,而正是这种畸形,驱使他们不择手段、成为改变历史的人。
若驱动历史进程的人不变,则与历史达成和解,某种程度上是个无解而无尽的问题。在此之前,PTA 的角色们和多数美国人一样,只得不停流浪。
流浪的人
《一战再战》改编自美国作家托马斯·品钦于199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葡萄园》。而这并非PTA第一次改编品琼的小说。
品钦的作品向来以混乱与庞杂闻名。可见或不可见的目的、持续与四散的线索……在叙事中随处可见。而PTA的改编,可谓某种相当切题的演绎。
在影片中,PTA将视线投向那些游离在主流之外的边缘个体,这在他早期描绘色情产业的《不羁夜》中就已显现。
PTA十分善于将个人故事置于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,将角色与历史时刻精巧地勾连起来,并始终对美国的政治现实有着强烈的敏感度,保持着某种一种中立偏左的微妙平衡。
「左与右」在叙事的激烈冲突下,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,加之PTA特色的异域风情审美,这样的叙事本身,已经成为某种类型。
PTA曾说,他「我并不认为超级英雄会毁掉电影」,但在他的电影中,却鲜少见到英雄。男性自我的挣扎与斗争,俨然已经成为 PTA 作品的母题。
他们常具有异常强烈而相似的性格与情感模式:用放浪不羁掩盖软弱、迷茫,在混乱无序的生活中漂流,总想用力抓住些什么,却总是徒劳无功。
孤独-流浪-救赎,似乎成了PTA影片中主角们的「标配」,也辐射出美国的文化风貌与历史凿痕。但他的独特性在于,温和地直面、处理人性中软弱的部分。

《一战再战》中的帕特,从意气风发的革命英雄,到大腹便便的单身爸爸。背不熟安全手册、记不住暗号、跳不过逃生的屋顶、轻易便被电击枪撂倒、飙车会花眼……像每个狼狈而力不从心的中年人,早已没有了半点理想主义的影子。
被曾经的同伴盛赞「他曾是个英雄」时,当下的帕特,却是个穿着睡衣、屁滚尿流在地上爬、躲避追捕的大叔。面对岁月、生活,他无能为力、束手就擒,只能屈服于无常,随波逐流。
这种「随机性」本身,也反映着整个美国社会在变迁中的心理变化。无论是对未来的无所适从,还是对过去的浓厚缅怀,都能在PTA的作品中捕获不少线索。
而这份「随机性」背后的动机与推力,似乎是时代进化下,再合理不过的产物。父位失职、母位模糊……晚期资本主义带来经济问题与心理状态的改变,同时也暗示了当下对于历史意识的丧失。
未来
《一战再战》中,PTA灵活地运用多线叙事,平行展开多线程剧情,构建了出一言难尽的世界。
对于历史、现实展现出清醒与悲观的同时,PTA心中仍抱持某种浪漫主义幻想:若流浪注定持续下去,唯有爱,能让人们找到方向与意义所在。
相比于之前几部作品,《一战再战》显得更加温柔。
当角色代表的群体,所面对的问题,在历史上注定无解;当软弱的个体,在时代无常的洪流中,不知如何自处时,PTA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:家庭。

帕特在逃亡中,曾短暂地进入Sensei创造的移民地下社区。那里拥挤、贫穷、简陋,但与看起来冰冷潮湿的边境的收容站截然不同。柔和的暖光和大片热烈的暖色调给人带来关于「家人」的希望。
Sensei身为拉美裔,教黑人学生亚洲空手道、帮白人父亲找到女儿……这种多文化融合下的温暖与包容,对于帕特而言,也许比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更有力量。
而当一切结束时,帕特和女儿又回到了曾经的家、回归了一如往常的生活,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他们没有搬家、恢复了过去的装修,帕特开始学着使用智能手机……这并不合逻辑,但很符合人性。时代在变、革命在循环,但家,是触手可及的安全之所,在混乱与狼狈中,如灯塔般,微末地照亮着生活。
在访谈中,PTA直言「让汽车坠落,或大搞爆炸场面很好玩。但真正让人感到兴奋和满足的,是角色之间亲密的关系」。
当信仰崩塌、理想破灭,情感成了唯一可被信任的真实。此处的政治,不在体制之上,而在生活缝隙中──在一个人于狼狈之中,依然愿意去爱、去承担之中。
与其说《一战再战》的政治性是宏观的政治现况,不如说它体现在家庭与个体的关系之中——情感与伦理层面的政治。PTA的镜头最终指向家庭,指向人与人之间的连结。
一如被「暗号」困住的帕特,最终没有和女儿对上暗号。而是以「我是爸爸」的家庭关系,替代了革命盟友关系。
作为「美国三部曲」的第三部,《一战再战》的最终信念,不再是所谓的革命,而是爱。在这个撕裂的年代,PTA以影像回应现实,让电影重新成为对时代注脚。
当帕特数隔多年,面对新的挑战,再度高喊「革命万岁」,那声呼喊早已超越政治,成为情感的释放与自我救赎。革命在此转化为寻找生命意义的方式,更是一场无声的内在抗争。
尽管他最终还是一事无成,尽管下一代的革命还没结束,尽管历史、革命是个循环……他们都在家中,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,找到了安全感。